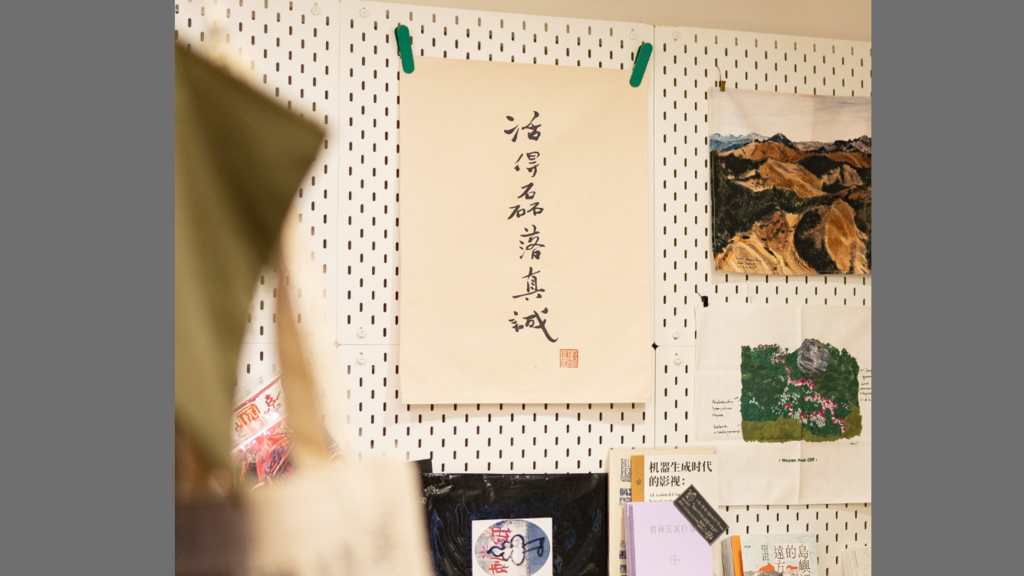
RFI:我們都知道,疫情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移民潮。而我觀察到,恰好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,你們在荷蘭開了“飛地”這家書店。
徐進:這個巧合背後,我覺得其實也有某種必然性。就像你剛才提到的,巴黎現在有很多中文書店,而事實上大多數都是近幾年才出現的,我也稍微了解過一些情況。放眼整個歐洲,乃至更廣泛的全球範圍來看,無論是美國還是加拿大,在疫情之後都出現了很多新的書店。
當然,也有一些書店因為經營上的困難而倒閉。但與此同時,越來越多人開始嘗試開設線上書店。比如在英國,各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情況,你在“小紅書”或者其他平台上搜尋一下,就能發現不少。
我覺得這其實反映了一種現象:就像你所說,在這一波華人新移民浪潮中,新移民群體對原本文化生活的渴望正在增強。這也是對過去移民生活刻板印象的一種打破,大家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於中餐館這樣的傳統行業。當他們想要創業、探索新的方向時,也開始嘗試一些既有商業性、又具文化性的項目。
“飛地”在各個地方的出現,其實正是在這樣一個全球書店復興的大背景下產生的。它的出現也許是偶然的,但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,它所代表的文化需求和發展方向卻是必然的。
RFI:那借這個話題我想問一下,其實開這樣一家書店,可以讓更多當地的華人有一個公共空間,能夠一起思考、交流一些與自身處境密切相關的問題,比如移民的處境。我很好奇的是,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說:“既然我已經移民海外了,那我就要在這裡紮根。我既然要紮根,就應該努力學習當地語言,融入當地社會,應該去當地書店、讀當地書。”那為什麼對於一個“離散的人”來說,母語的閱讀依然重要呢?這種重要性一直都存在嗎?還是說在新冠疫情之後的新移民潮中,這種文化需求變得更加強烈了?
張潔平: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。
首先,這兩種需求,也就是融入當地社會和保持母語文化,並不矛盾。你完全可以在荷蘭、法國或紐約這樣的地方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,同時保有自己的母語文化。這個事情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極端。並不是說我每天逛中文書店,就成了一個只能待在唐人街、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人。我覺得那是一種刻板印象。
其次,我認為對於離散的華人來說,堅持母語閱讀的重要性有兩個層面。
這也是“飛地”的一個特色。你剛才提到我們有很多繁體書,其實最簡單的做法,就是把同一主題下的書,無論是繁體、簡體,還是來自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出版的,都放在同一個書架上。別人會覺得這很稀奇。但對我們來說,這正是我們希望呈現的狀態。中文因為種種歷史與政治的原因,往往被迫變得高度政治化,但它本來就是一種彼此都能讀懂的語言。
我希望“飛地”能在一個相對自由、沒有包袱的空間裡,重新呈現華語世界應有的多樣性與豐富性。這種體驗,其實在我們原來的生活環境中是接觸不到的,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海外必須“補上的一課”。
我覺得這正是當代人對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種新的回應方式。
RFI:非常感謝你的回答,我覺得特別好。那我想最後再問一個問題吧。之前在很多場合你都提到過,比如我聽過你的採訪時你說,開書店其實也是一種“在另一個地方重建中國”的嘗試。其實我也聽到過一些不同的聲音,有些人覺得,他們離開中國後,終於能自由地表達了,但與此同時,他們的聲音似乎又沒有被當地社會真正聽見,也難以傳回國內。那麼,在這種情況下,“重建中國”這件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?
張潔平:謝謝,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。 其實,“重建中國”這個概念非常容易被誤解,所以我一般不會太強調這個詞,雖然每個人在使用它時都有自己的理解。
比如說女性的處境。我在東京的感受特別深,東亞女性真的是“同一國人”。有一次,一個香港女作家的書在日本出版,一個懂中文的日本讀者讀完哭了,一個在韓國留學的中國女孩也覺得特別有共鳴。你就會發現,東亞女性的經驗是相通的。
所以對“飛地”來說,我們希望在活動中討論的,不是抽象的、宏大的“國家問題”,而是這些能夠讓人彼此相連的“共同問題”。
張潔平曾在其他的採訪中表示,她理想的社會是大家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身份認同,非常不同的政治觀點,但當大家對某一些話題的知識有相似的興趣時,大家就有機會走在一起,而飛地就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空間。當不同的人面對面坐下時,大家伸手去拿同一本書時,儘管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可能有非常不一樣的政治觀點,但他們拿那一本書的那一刻,他們看了彼此一眼,那個信任感就升溫了,開始願意聽對方說兩句。也許第一次只是萍水相逢,參加幾次活動後,他們就成了朋友。而她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重建中國不再是一個政治實體的概念,而是擴展成為每一個人具體的、可以踐行的行動本身。
以上就是本期的中華世界,感謝Julie和Souringa提供的音訊技術支持。













